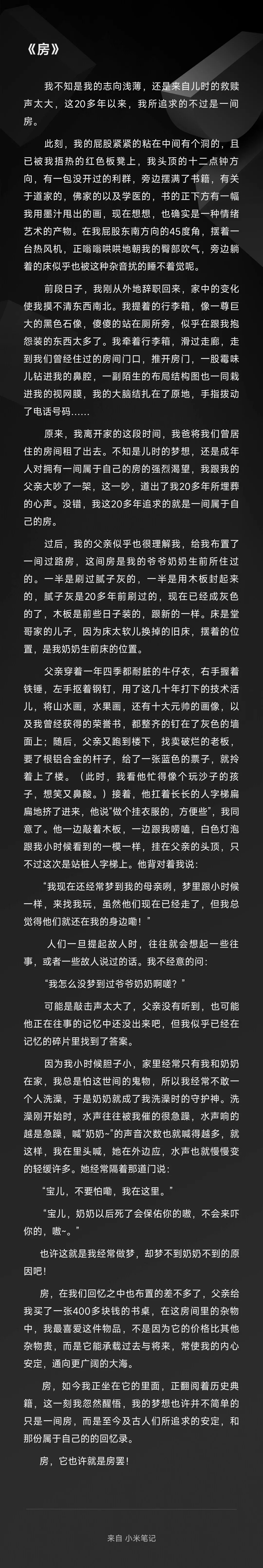@ 炳 子
我不知是我的志向浅薄,还是来自儿时的救赎声太大,这20多年以来,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一间房。
此刻,我的屁股紧紧的粘在中间有个洞的,且已被我捂热的红色板凳上,我头顶的十二点钟方向,有一包没开过的利群,旁边摆满了书籍,有关于道家的,佛家的以及学医的,书的正下方有一幅我用墨汁甩出的画,现在想想,也确实是一种情绪艺术的产物。在我屁股东南方向的45度角,摆着一台热风机,正嗡嗡哄哄地朝我的臀部吹气,旁边躺着的床似乎也被这种杂音扰的睡不着觉呢。
前段日子,我刚从外地辞职回来,家中的变化使我摸不清东西南北。我提着的行李箱,像一尊巨大的黑色石像,傻傻的站在厕所旁,似乎在跟我抱怨装的东西太多了。我牵着行李箱,滑过走廊,走到我们曾经住过的房间门口,推开房门,一股霉味儿钻进我的鼻腔,一副陌生的布局结构图也一同栽进我的视网膜,我的大脑结扎在了原地,手指拨动了电话号码……
原来,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,我爸将我们曾居住的房间租了出去。不知是儿时的梦想,还是成年人对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的强烈渴望,我跟我的父亲大吵了一架,这一吵,道出了我20多年所埋葬的心声。没错,我这20多年追求的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。
过后,我的父亲似乎也很理解我,给我布置了一间过路房,这间房是我的爷爷奶奶生前所住过的。一半是刷过腻子灰的,一半是用木板封起来的,腻子灰是20多年前刷过的,现在已经成灰色的了,木板是前些日子装的,跟新的一样。床是堂哥家的儿子,因为床太软儿换掉的旧床,摆着的位置,是我奶奶生前床的位置。
父亲穿着一年四季都耐脏的牛仔衣,右手握着铁锤,左手抠着钢钉,用了这几十年打下的技术活儿,将山水画,水果画,还有十大元帅的画像,以及我曾经获得的荣誉书,都整齐的钉在了灰色的墙面上;随后,父亲又跑到楼下,找卖破烂的老板,要了根铝合金的杆子,给了一张蓝色的票子,就拎着上了楼。(此时,我看他忙得像个玩沙子的孩子,想笑又鼻酸。)接着,他扛着长长的人字梯扁扁地挤了进来,他说“做个挂衣服的,方便些”,我同意了。他一边敲着木板,一边跟我唠嗑,白色灯泡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,挂在父亲的头顶,只不过这次是站桩人字梯上。他背对着我说:
“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的母亲咧,梦里跟小时候一样,来找我玩,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走了,但我总觉得他们就还在我的身边嘞!“
人们一旦提起故人时,往往就会想起一些往事,或者一些故人说过的话。我不经意的问:
“我怎么没梦到过爷爷奶奶啊嗟?”
可能是敲击声太大了,父亲没有听到,也可能他正在往事的记忆中还没出来吧,但我似乎已经在记忆的碎片里找到了答案。
因为我小时候胆子小,家里经常只有我和奶奶在家,我总是怕这世间的鬼物,所以我经常不敢一个人洗澡,于是奶奶就成了我洗澡时的守护神。洗澡刚开始时,水声往往被我催的很急躁,水声响的越是急躁,喊“奶奶~”的声音次数也就喊得越多,就这样,我在里头喊,她在外边应,水声也就慢慢变的轻缓许多。她经常隔着那道门说:
“宝儿,不要怕嘞,我在这里。”
“宝儿,奶奶以后死了会保佑你的嗷,不会来吓你的,嗷~。”
也许这就是我经常做梦,却梦不到奶奶不到的原因吧!
房,在我们回忆之中也布置的差不多了,父亲给我买了一张400多块钱的书桌,在这房间里的杂物中,我最喜爱这件物品,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比其他杂物贵,而是它能承载过去与将来,常使我的内心安定,通向更广阔的大海。
房,如今我正坐在它的里面,正翻阅着历史典籍,这一刻我忽然醒悟,我的梦想也许并不简单的只是一间房,而是至今及古人们所追求的安定,和那份属于自己的的回忆录。
房,它也许就是房罢!